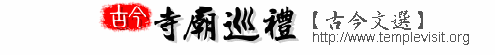|
不要錯失良機
一九五三年,我常在宜蘭弘法,後來創設了一個幼稚園,那時有七、八位年輕小姐擔任老師。我見他們很有學習性,便省吃儉用,湊出一筆經費,作為車資,經常送她們到台北、板橋接受幼教師資的講習。她們每每在即將出發之前,一再問我:「師父!我們真的要去嗎?我們走了,誰來教幼稚園呢?」我回答她們:「我也會帶幼稚園,妳們快去吧!不要錯失良機!」她們學成回來之後,繼續擔任教職,將幼稚園辦得比以前更有聲有色,學生人數竟達五百餘人之多,在當時可說是全國之冠。後來她們陸續隨我出家,其中就有現在的慈嘉、慈容、慈惠。
十多年後,在佛光山草創初期,正是財務最拮据的時候,我又陸續送慈惠、慈嘉、慈怡、慈莊、慈容等人去日本留學。她們甚至在臨上飛機時,頻頻問我:「師父!我們一個個走了,您一個人怎麼能料理開山那麼多事情呢?」我依然以平靜的口氣回答她們:「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妳們不要猶豫遲疑,錯失了良機!」她們畢業歸國之後,幫我辦理各種文教事業,佛光山因此而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後來,我又送了一些徒眾繼續到世界各國去深造,但也有一些沒有條件留學的弟子,自己前來要求留學,我回答他們:「你們留在山上好好學習行政、法務,不要錯失良機!」一些弟子聽從我的勸告,繼續留在佛光山多方參與,現在都已是住持一方,「良機」無限,他們都很感謝我當年的苦心;一些弟子一意孤行,後來學無所成,悔不當初,才知道自己沒有條件,即使爭取到機會,也不是「良機」。所以,什麼是「良機」?我覺得:有未來性,能利己利人的機會,才是「良機」。回想我並無聰明才智,境遇也不是很好,但是仍能為佛教創出一番天地,「沒有錯失良機」正是重要因素之一。
即以讀書深造為例,過去我還在焦山佛學院念書的時候,曾有機會可以進國立師範學院念書,但師父卻以苛責的語言回絕了我,而送我的師弟今慈去念大學。後來師弟還俗,我才恍然大悟,偉大的師父嚴厲地罵我,是故意用一種激烈的方式,讓我「不要錯失良機」。
來到台灣之後,我遇到曾在天寧佛學院擔任教務主任的圓明法師,一九五一年,他獲得中國佛教會的獎學金赴日留學,大家對他寄予厚望,只可惜他也像許多到日本留學的中國年輕比丘一樣,滯留當地,後來聽說在大學教書,兼開補習班,將會終此一生。記得當時的我居無定所,一文不名,既沒有圓明法師這麼好的機緣,也沒有同門師兄弟得以依靠,但憑一股愛教熱忱,在各處弘法佈教,卻因此結下許多法緣,開拓日後廣大的人生。所以,機會來了,不見得好,如果一念之差,隨波逐流,反而「錯失其他真正的良機」;沒有機會,卻能腳踏實地的做好自己的本份,就是一種潛在的「良機」。
四十年前,因為我經常為了護持正法、釐清佛教的原則,而在報章雜誌上掃除邪見;又寫了一本《釋迦牟尼佛傳》,引起日本大正大學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寄給我一紙博士班入學通知單,希望我前往就讀。當時我想:這個機會實在太好了,我要努力讀書,將來學成歸國,服務大眾,好為中國比丘爭一口氣,讓大家知道不是每一個人到了日本就會變節還俗。既而又想:「我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在台灣這片佛教沙漠之中開闢了一些綠洲,如果我去了日本,有誰能繼續我的願心,將菩提種子遍撒台灣各個角落呢?」正在猶豫的時候,高雄萬隆醬園的朱殿元居士得知這個消息,焦急地跑來問我:「你已經是我們的師父了,為什麼還要去日本當學生呢?」我突然醒悟:「此時此刻,我何必為了博士虛名爭一口氣遠赴東瀛呢?我留在台灣好好耕耘這一片淨土,如果能讓佛教擁有光明的前途,就足以證明比博士學位更為重要!」後來事實證明:我雖然失去了深造的機會,但是我並「沒有錯失良機」。在此二十年後,美國東方大學頒給我榮譽哲學博士學位。這麼多年來,我看盡世事起伏,往往發現:人,之所以會「錯失良機」,大多在於私心自蔽,以致自他受害。原來所謂「良機」,是要自他歡喜,彼此有益,公私兩利才可。
像太虛大師因為在中日戰爭期間曾經組團到國外宣揚國威,揭穿日本對我國的侵略宣傳,獲得英、美、錫、緬等國的支持,使得八年抗戰終於勝利成功,所以無論在朝在野,聲望都很高,這本來是振興佛教的「良機」,但由於佛教守舊派的僧伽不肯合作,以致功敗垂成,令人扼腕。記得當時我等一批僧青年為了響應他的號召,曾在南京組織佛教青年會,準備如火如荼,有一番作為,可惜後來因為會內有人搗蛋而使會務告終,就這樣丟失了「良機」,當時我的心中真是悲憤填膺,但又徒呼奈何!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在佛教地位低落的當時,曾遭遇一段困厄的時期,但我並不氣餒,依然為弘揚佛法而奔走,或救濟風災、震災,或到監獄講經說教,或到鄉間海邊弘法,或編印發行雜誌,或許是因為如此,得到多位教界前輩的垂愛,給予我發展的機會,只可惜因緣不具,仍然不能圓滿所願。像慈航法師曾介紹我到嘉義天龍寺去當住持,儘管老住持能之法師已然承諾,但由於沒有得到寺內全部委員的同意,所以我默然不敢承受;一善堂的負責人吳隨居士也想將堂務交給我接管,然而他的親族很多,意見不一,所以我婉拒了他的美意;紐約大乘寺的主事者應金玉堂有意將道場交給我,並承諾我辦移民二十人前往美國,也聽說他家人有意見,因此我沒有動身前往接任。許多人說:「你好傻!既然住持人都同意了,你何必管那些閒話,而白白浪費弘法利生的機會呢?」我告訴他們:「機會如果是勉強成事,而非眾緣和合,就不是『良機』,寧可失去的好。」當時心想:「慚愧自己無福無德,惟願效法前輩給人因緣的精神,並且設法讓大家皆大歡喜,使之成為別人的良機。」或許是因為事先設想周到,我推薦同道至各處住持道場,例如我推薦月基法師到高雄佛教堂、成一法師主持頭城念佛會、真華法師主持羅東念佛會、煮雲法師到虎尾念佛會,都能一一成功,眼看佛法傳播日廣,心中好不歡喜,深深感到:「良機」不一定要自己擁有,同道們遍布各地弘法,促使佛教興隆,不但大眾受益,身為佛教徒的我們也都可以跟著沾光,不是很好嗎?一向以來,我本著這種為大家製造「良機」的理念立身行事,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不知為自己創造了多少「良機」。
想當初沒有人願意留在宜蘭弘法,因為大家都覺得這裡地方偏僻,設施落後,並非「良機」,而我卻能在此地一待數十餘年,將蘭陽佛教帶動起來,使蘭陽弟子遍布全省,甚至全世界,最主要是因為我只想到要為宜蘭人創造「良機」,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尊榮利益。
開闢佛光山亦然,那時曾有人勸我:「這片山林地質不佳,風水又不好,難怪沒有人要,尤其高屏溪就在山的前面流過,將來錢財全部都會流走。」我告訴他:「我覺得溪水流過去很好,這代表法水永長流。」等到我力排眾議,將佛光山建好了,卻又聽到別人說:「你真會看風水,揀到一個『良機』,我今天繞山走了一圈,發現整個佛光山是蘭花瓣的形狀,好一塊福地啊!」其實我那裡懂得什麼風水,當初來此,既是為了找一片便宜的山林可以建寺辦學,也是因為看中它在鄉下,可以讓我避免許多無謂的應酬,而能專心一意為佛教培養人才,創造更多發展的「良機」。結果,我真的「沒有錯失良機」!可見「良機」處處有,地理風水也是唯心所造啊!
一九七一年,中美斷交,台灣退出聯合國之際,佛光山上正大興土木,興建朝山會館,由於必須移山填溝,所以花費甚鉅,雖然建築商特別通融,答應我的請求,讓佛光山賒欠鋼筋水泥款,但是那段日子還是十分難捱。當時有人告訴我,時局不好,很多人都在打算移民,勸我也不要再進行了。我回答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我建朝山會館,是因為看到信徒每次來山,連食宿的地方都沒有,並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沒想到朝山會館建好之後,給予信徒莫大的方便,來山的人因而越來越多,我用佛法接引他們,奠定了佛光山的發展基礎,至今想到此事,還很自豪從頭到尾都「沒有錯失良機」。
美國弘法之初更是困難重重。記得慈莊、依航才到洛杉磯籌備建寺不久,就飽受民眾嚴重抗議,加上當地美國人不了解正信佛教,而一些異教徒又故意從旁毀謗。從台灣前往美國探親的信徒們,回來之後,向我描述當地情況直可以「風聲鶴唳」四個字來形容,雖說知徒莫若師,我相信弟子們一定能夠完成使命,但我還是打電話告訴他們:「只要抱定奉獻的心意,和大眾結緣,就是『良機』,不要錯失了!」十多年寒暑過去了,她們以無比的誠意及耐心與當地人士不斷地溝通交流,提供服務,果然不負眾望,最後附近的居民竟然全力支持西來寺的建設。一九八八年落成之日,嘉賓雲集,有一位記者問我:「西來寺能為美國帶來什麼?」我告訴他:「西來寺不但開放給僧信二眾作為禮佛淨修的場所,也提供各界及社區人士舉辦有意義的活動,我們希望以熱忱的服務,用佛法的文化為大家帶來各種『良機』。」
真的,我在各地弘法度眾所抱持的就是這種給人「良機」的心情,也因此有難不覺難,有苦不覺苦。像香港過去有些人基於對賭博賽馬的迷信,見到出家人非常排斥,許多外地法師不敢久留,但我仍派依如到那裡,親近當地長老大德,一再告訴他要不計辛勞,默默服務,他善解我意,十年有成。我在香港講經,從沙田大會堂講到紅磡體育館,聽眾一年比一年盛況;後來應當地信徒要求,興建道場,從佛香精舍到佛香講堂,法務一年比一年昌隆;後來當地張蓮覺居士創建的東蓮覺苑委託我派人管理,荃灣的弘法精舍提供給我作為教育場所;香港人對出家人也一改以往的態度,對他親切而有禮。尤其近幾年來,我在世界各地弘法,發現香港移民最為熱忱,不但出錢出力,而且從不居功。問起他們學佛因緣,許多來自佛光山最早辦的佛香精舍,讓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大家彼此都「沒有錯失良機」。
其他弟子如慧禮、依來等人在南非建寺時,正值種族糾紛最嚴重的期間;永光、永寧等人被派去菲律賓弘法時,也是內亂暴動最厲害的時候。尤其當地人大都信奉耶教,「佛教」是一個嶄新的名詞,可以說種種情況對我們都十分不利。幸好派在當地的徒眾都具有共識,認為越苦難的地方,越需要佛法,所以寧可為法捐軀,也「不要錯失良機」。只見他們不顧眾人奇異的眼光及嗖嗖的槍聲,在街巷市場弘法佈教;不計辛苦疲憊,跋山涉水到鄉間發放賑濟品,短短幾年間,大家對佛教都刮目相看了!一九九七年春節,菲律賓拉采瑞茲主教邀請在馬尼拉佛光山講堂僧信二眾至岷侖洛天主教堂,共同為社稷祈福,因屬首次,成為媒體競相報導的新聞;前不久南非總統曼德拉先生也派人到約翰尼斯堡的南華寺訪問,也是轟動一時。凡此都說明了「良機」固然有時候是天賜的佳緣,但更多的時候,是必須付出相當的努力,才會降臨在我們的身上。
我祖籍揚州,居台半世紀,適逢中國多難,戰亂頻仍,我在青少年時期,歷經顛沛流離,憂患相煎的歲月,目睹殺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慘狀,身遭骨肉離散,天人永隔的悲劇。多年來,我深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世代的對立意識已然雲淡風清,兩岸彼此的隔閡才是大家心中未癒的傷痕。我有意促進彼此的溝通交流,卻苦無機會。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參加泰王六十歲大壽的慶典,才有了轉機。當時,大陸方面的代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長老暨其夫人也應邀在座,但礙於當時情勢,我們彼此無法交談。就在典禮剛開始不久,趙夫人突然咳嗽起來,坐在後面的慈惠法師拿出一顆止咳糖遞給她。趙樸老當晚回贈大作以示感謝,我覺得「良機不可錯失」,殷勤接待,在暢談之際,欣知彼此在許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識。後來聽說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前兩次大會因兩岸名稱問題,弄得場面十分尷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屆大會的主辦權成為燙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機正是「良機」,「不可錯失」,遂主動爭取由西來寺承擔這個任務。為了加速完工時間,不惜加倍給付建築商趕工費用,好讓西來寺的工程能及時完成,趕上大會的召開。至於兩岸的佛教會名稱,我想了一個折衷的方法,即中文名稱──「中國北京、中國台北」照樣沿用,英文譯名改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和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自以為如此設想十分周到,但還是經過一番曲折,多次協商瀕於破裂。為了不要因這一點點問題而「錯失良機」,我一次又一次居間調和,終於化解僵局。當我在大會開幕典禮中宣佈「海峽兩岸的團體第一次坐在同一個會議廳裡開會」時,三十餘國,八十幾個佛教團體,五百多位代表,長時間報以熱烈掌聲。由於這次的成功,拉近了兩岸佛教界的距離,趙樸老邀我去大陸訪問。翌年(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率領正團七十二人,副團五百人組成的「國際佛教中國弘法探親團」成行,趙樸老在北京機場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我也深深地感歎著:「良機」不易,幸好「沒有錯過」,否則不知道還要等到何年何月。
成立佛光大學及佛光衛星電視台的情況也有點相似,雖說早年就有的構想,但那時法令並不允許;等到法令開放,一時之間,無人又無錢,但我還是緊急設法,在短期間內籌辦起來。有人說:「何必那麼辛苦,等到以後一切具足了因緣再辦,不是更從容嗎?」我覺得:世事無常難料,把握當下的「良機」,才不會導致日後的遺憾,更何況以佛教精神辦理的大學和電視台,可以及早為社會注入清流,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總之,「良機」稍縱易逝,不可不慎!翻閱中外歷史,宋高宗因為聽信奸人秦檜的讒言,將岳飛斬殺,錯失了反攻的「良機」;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相,銳意新政,但由於行法苛嚴,觸怒了士大夫、商主,引起大力反彈,反倒阻礙了改革的「良機」;而齊桓公卻因不計前嫌,重用管仲,開創了春秋霸業的「良機」;福特則因善用父親給予的一塊錢美金,成為建設汽車公司的「良機」。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一句話、一個環節、一個人、一文錢,乃至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足以導致成敗的關鍵,豈能輕乎渺視?
在中國有許多要我們把握良機的格言,很值得我們銘記在心,像「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是在教導為人子女者不要錯過行孝的「良機」;「苦口良藥,忠言逆耳」,是提醒在迷途的當局者不要錯過忠言的「良機」;「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是在警惕青少年們不要錯過青春的「良機」;「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是在勸告行為放逸的人不要錯過行善的「良機」。佛教的經典裡,鼓勵大家不要錯失良機的字句更是俯拾皆是,像《華嚴經》的「不忘初心」,《八大人覺經》的「不念舊惡」,《維摩經》的「不請之友」,《大乘起信論》的「不變隨緣」,都是「把握良機」的最佳法門。總之,沒有機會的時候,廣結善緣;機會來臨的時候,及時掌握,就不會有「錯失良機」的遺憾了。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