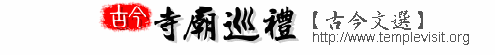|
沒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國法身寺負責國際弘法部門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會的會長帕拉普先生將佛牙恭送到臺灣的時候,曾經來山住了幾天。有一天,她說:「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歡喜、安住,因為我在法身寺不是從事職業,而是一件沒有待遇的工作。」我雖然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還是繼續問她:「沒有待遇的工作有什麼好處?」她說:「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種職業,我會計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歡喜。現在因為沒有待遇,我覺得是法身寺的法務,是我良心的責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覺得沒有待遇的工作比職業性的工作要快樂的多。」善哉斯言!難怪多少年來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樂而忘憂,原來她已經深入快樂工作的三昧了,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眾從信仰裡,從服務中所激發的法喜禪悅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門的長老職事,為什麼能數十年發長遠心,為佛門奉獻,無怨無悔?仔細想來,不正是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只求佛法能發揚光大嗎?像心平原本在中華印刷廠服務,慈莊原本在蘭陽女子中學服務,慈惠在稅捐處服務,慈容在製藥公司服務,心定在郵局服務,蕭慧華在電信局服務……,三十年前他們為了信仰,不惜辭去千元待遇優厚的工作,投入佛門的弘法事業,每月只領取區區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發揮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數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為他們弘法利生的代價不是外來的金錢數字,而是內心的功德法喜。
記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來寺參加佛教會議時,看到住眾從早到晚忙得如此歡喜,不禁慨嘆自己經常找不到一位樂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於是問我其中有什麼秘訣?我說:「這是因為我以『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所做的一切都是『沒有待遇』,心甘情願的工作。」回想多少年來,我經常想到自己只是大眾中的一個,所以從來不以師長自居,命令別人做事,結果大家對於這種沒有命令,「沒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熱心。
像在臺灣榮民總醫院為我心臟開刀的張燕醫師、美國皮膚科的沈仁義醫師、眼科的羅嘉醫師、牙科的李錦興醫師,不但視我如親,耐煩問診,即使聽說任何一個佛光山的住眾生病了,他們都會自動放下手邊的工作,親為治療,長遠以來,從不接受金錢或物質上的「待遇」,比「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認真。
「沒有『待遇』的工作做起來更加起勁。」臺北佛光青年團團長黃金寶如是說。看著她領導一群青年幹部,在公暇課餘,從普門寺做到臺北道場,從臺北道場做到佛光山,任勞任怨,十數年如一日,不禁讓我回憶數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許多不求「待遇」的義工,那種為法忘軀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像李決和居士在宜蘭雷音寺為我義務擔任總務主任二十年以上時間,後來隨我出家,法名慧和;省議員陳伯汾先生為佛光山萬壽園和佛光大學的建校工作,在臺北、臺中忙碌奔走;此外從早期的林松年、郭愛、陳慈如、洪呂淑貞等,到近來佛光山各別分院的義工,如臺北的蘇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許卉吟,基隆的孫翠英、李鳳英,以及臺灣中部的沈尤成、洪嘉隆、賴義明,臺灣南部的曾進*?、陳順章、葉惠貞、蕭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溫哥華的趙翠慧,波士頓的馮文鑾,休士頓的趙辜懷箴,洛杉磯的陳居,香港的嚴寬祜,馬來西亞的陳瑞萊,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劉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聖保羅的張勝凱,南非的熱內等。尤其,總統府資政吳伯雄先生公開表示自己是佛光山臺北道場的義工,要「將政治擺兩邊,佛教放中間」,更是令人感動。
近年來,我在臺北道場出入頻繁,常常天還沒亮,就看到義工們已忙著擦窗、洗廁、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場的工作就搭公車去上班,有的繼續留在道場值日服務,其中有許多人在家裡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紳、千金嬌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從事金剛、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沒有道情,那裡會有人肯如此熱心?所以我常說:「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
在佛光山的職事員工達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沒有假期,每天供應信眾飯食、帶領香客參觀、照顧佛殿香火、從事文教工作之餘,還得自修佛學,早晚課誦,朝醒夜寐,無時無刻不在分秒必爭中度過,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這種「沒有待遇的工作」讓心靈更充實,更快樂。因為在「沒有待遇的工作」裡面,有自己的尊嚴,有奉獻的誠意,有發心的喜悅,有無限的價值。
佛光山佛教學院的學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務,寒暑假有勞動,過年過節還得為眾忙碌,有時第二天就要考試了,但為了讓來山的信眾都能心無旁鶩,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擻地從事行堂、典座、香燈、知客等工作。有時我和老師們說:「學業要緊,應該讓學生有多一點時間準備考試。」沒想到學生們卻說:「我們在佛門裡修行,要為弘揚佛法多做一點事情,佛光山是選佛場,我們要經得起佛陀的考試。」──「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張滿分的成績單!
記得過去在臺灣,著名的臺南大仙寺,裡面有三百多位住眾,他們寺院規定在做苦工十五年後,可以換得一間房間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眾,連房間的觀念都沒有,每天沉醉在奉獻的法喜中,像慈莊在美國開山時,曾經以馬場為家;滿徹初到德國時,以車庫為房……。如果不是諸佛菩薩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讓四眾弟子攜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淨土?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獲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實則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黃世樑和林秀蘭夫婦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蘭度化的信徒,那時他們還沒結婚,雙方都曾要求隨我出家,但我當時沒有道場,無法教養他們,所以勸他們在家結婚一樣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後來他們雖然成家立業,但雙方約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養子女。當我建佛光山時,他們結束事業,和我共同開山,二十餘年來,黃先生從事水電修繕,黃師姐為大眾服務,不但不要求待遇,還將臺北房屋的租金捐獻給各種佛教事業。發菩提心容易,發長遠心難;做沒有待遇的工作容易,作幾十年還能保持如此歡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臺北的工商界為了要求加薪,紛紛遊行街頭,示威抗爭,一時之間,震動了整個臺灣。我在一次集會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員工幽默地說:「你們也可以搖旗吶喊,走到大雄寶殿或朝山會館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為大家不免也會對「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負責清潔掃地的老先生起身發言,說道:「我們不是為待遇而來的,我們是為歡喜和功德而來的。」我問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麼歡喜呢?」他說:「法師們遇到我們的時候,都稱我們『老伯』,而且對我們微笑、尊重,種種關懷,在這裡工作,有很大的尊嚴,有很多的喜悅,這些就是無上的『待遇』,為什麼要去遊行增加『待遇』呢?」
「沒有待遇的工作」蘊含了多少的樂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沒有暑寒假、沒有年節,也從來沒有要求過「待遇」。在大陸做小學校長的時候雖有待遇,但我沒有領過一毛錢薪水,因為我和師兄說:「校長的薪水,請您一半交給常住,一半交給我的母親。」
由於十年叢林教育養成我沒有用錢的習慣,所以有「待遇」也像沒有「待遇」一樣。記得我初到臺灣,在臺灣省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時,那時發的錢,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單銀」,每個月可以領到單銀五十元。但是我都將這筆錢拿來訂佛教雜誌或購買圖書送給學生閱讀。
後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幾十年當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單銀,我用來添置弘法道具,率領青年到各處佈教講演。當時蘇澳到瑞芳所有火車站的站長都皈投三寶座下,宜蘭鐵路局運務段段長張文炳居士認為我們對宜蘭佛教有貢獻,因此每次看到我們一行多人搭乘火車到各地佈教時,都不收車票錢。讓我得以將省下的車資作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來,仍感念不已。佈教之外,我將單銀餘款購買紀念品、卍字項鍊和青年朋友結緣。那時耶教盛行,掛十字項鍊者比比皆是,這些可愛的佛教青年們卻將我送他們的卍字項鍊掛在頸項上,露在衣領外面,穿梭在機關行號、市街大道上,引來許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當時的情景,都不禁歡喜鼓舞,因為在那個佛教備受壓抑的社會裡,在那種民風保守的年代裡,他們這種大膽的行動是多麼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開山之初,每逢周末,臺北等地都有許多人成群結隊朝山,在早課時皈依三寶,我的紅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沒有接受待遇的習慣,所以就將紅包聚集起來,為大眾購買桌椅、拜墊。幾十年來,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墊,無一不含藏了我誠摯的心意,偶爾在內心也會洋洋自得。
我經常應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專院校講學,我一概拒絕酬勞,但企業行號、公司工廠等地方,因為是生產單位,我恐怕不接受顯得太過矯情,所以收下來之後,就盤算如何用之於大眾。甚至於臺灣省省訓團公務人員集訓時,我是講師之一;成功嶺大專青年集訓時,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學、東海大學,我也曾擔任教席,像這些常態性上課的鐘點費,我都集合起來購買圖書,供大家閱讀。現在佛光山別分院幾十個圖書館裡都有我購買的書籍,當青年們閱讀時,雖然不知道書裡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內心的歡喜,卻依然是無與倫比的。
我曾經擔任中佛會理監事數十年,也曾在臺灣省佛教會各支會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多次,都沒有待遇;甚至我擔任常務顧問、評議委員,也都是無給職;我參加各處道場開光剪綵,都不收車馬費。雖然做了多少「沒有待遇的工作」,初時默默無聞,可是為我一生帶來多少善緣。
我和發心的人一樣,一生樂於做社會的義工。我曾擔任蒙藏委員會的顧問、僑務委員會的委員、法務部的監獄教誨師,凡此都是「沒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歡喜,很自然,因為從過去以來,一直都認為服務大眾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裡的呼吸一樣,沒有特別的感覺。偶爾在過年或中秋時候,承蒙先總統蔣經國先生、總統李登輝先生派人送來一點禮品,我也趕緊以佛書相贈,表示禮尚往來。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辦《今日佛教》、《人生雜誌》、《普門雜誌》、《覺世旬刊》的時候,還要自己義務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購買郵票、車票、稿紙、信紙;我辦佛學院三十餘年,曾擔任無給職的校長、老師,不但不收學費,還供給學生吃住衣單等等。雖然都是一些「沒有待遇的工作」,但當我看到多少社會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麼報償都來得更加欣慰。
現在佛光山各別分院辦中文學校、才藝班,我希望他們不要收費,但徒眾卻說社會上請來的老師需要有鐘點費,因為「因果業報平等」固然是佛門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會的遊戲規則卻是「義務權利對等」,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順應時代需要,讓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個人認為想要未來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須提供權利、義務對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別人長期義務奉獻。
過去多少年來,我看到前來佛門發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會上年老退休以後,已經不計較,也不需要金錢來養活家人和自己,才將殘餘歲月的力量全心奉獻給佛教,自忖:「這樣的幫忙,能夠成就多少事業呢?佛門對於一些工作人員也應當給予合理的『待遇』。」所以當我成立普門中學、佛光出版社、普門雜誌、佛光大學……時,對於所聘的專職員工,都支付薪津報酬,因為有了待遇,才能解決生活問題,才能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為弘法利生而奉獻自己。如果個人不需要外財負擔家計,有了佛法,內心必定會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絕接受待遇,所謂「有無一如」,不執不拒,無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種修行境界。
此外,我認為:佛門對於一些學有專精,卻心甘情願在宗教裡奉獻,不要求待遇的人,也應該給予發展的管道。像高呈毅先生從經濟部高級工程人員之職退休以後,中國大陸邀請他前往指導長江三峽的建壩工程,但他卻婉辭這項待遇優渥的工作,寧願殫精竭慮發心參與策畫佛光大學的建校工程;嘉義東元電機公司的老闆游次郎先生放下嘉義救國團總團部總幹事的工作不做,自願監督南華管理學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國策顧問余陳月瑛女士為了佛光山的事經常到各個階層奔走發言,我曾取笑她說:「妳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聽到這句話,也莞爾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師、高雄的蘇盈貴律師、專科職校的陳潮派老師等保護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樣……。我想︰即使給予再優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獻身獻命的人。感念之餘,我對他們倍加敬重禮遇。從他們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沒有待遇的工作」實則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門中學教職員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學校來發給月薪,而佛光山徒眾沒有待遇,只有每個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門中學一位老師將薪水用罄之後,向佛光山一位職事說:「將你的三百元也借給我好嗎?」可見得有待遇的人,不見得有,不見得多;「沒有待遇」的人,也不見得少,不見得無。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傳授三壇大戒,邀請二十多個國家的戒師穿越千山萬水,前來擔任戒場教誡工作,從來沒有一個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為弘法利生而摩頂放踵,不計利益的美德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巴西佛光會的張會長不但捨宅為寺,又再添購大筆土地,計畫建設南美第一大寺,將來還要辦南美洲佛學院;美國休士頓佛光會的趙會長不但購地建寺,還到處張羅建設基金。現代居士大德為興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錢出力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數人緇銖必較的普遍心態,佛教的無相功德不是更豐富,更圓滿嗎?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窮,有盡;無,是無限,無量,無窮,無盡。「沒有待遇的工作」,實際上擁有了更多、更大、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不但個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開山建寺,也是「以無為有」,經常今日不知明日糧,日日難過日日過,正應了古人的詩偈:「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時時刻刻都覺得法喜充滿,希望無限。《般若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真是一點兒也不錯。所以,「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文不名,實際上是心甘情願、歡喜結緣的工作;「沒有待遇的工作」看起來一無所得,實際上才是真正能獲得功德法財的工作。
讓我們歌頌工作的權利義務有對等價值的同時,也禮讚「沒有待遇的工作」,因為那不但是佛教有緣人的本分,也是一種能讓自己擁有無限,獲益無窮的生活哲學!
(佛光卅二年-一九九八年八月)
|